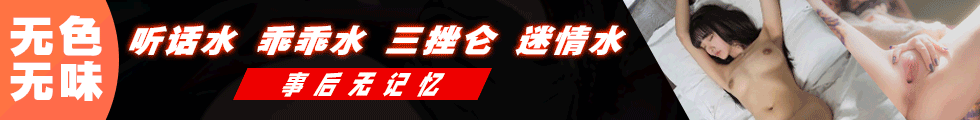花萌露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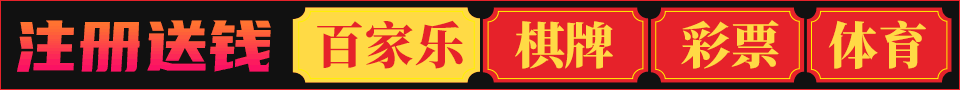

武侠古典 2024-03-14
诗云: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。
抛却给发妻,建荡逞色相。
黄天须有报,叫他尸抛荒。
话说历代君王俱知守成艰难,遂挖空心思欲网尽天下人才为他所用,故开科试以揽英才,另设举荐一途,后称「举孝廉郎」。一旦荐作「孝廉郎」,顷刻补人知县、知府候补名额,若逢圣上龙思浩荡,御笔钦点,顿时峨冠翎带,官袍加身矣!
平常百姓儿女,便存了侥?心肠,至小饱读圣贤书,平生做尽仁义事,希图博个好名誉,万一机缘凑合,岂不久仕为官,光宗显姓,青史驻名乎!却有极贪图富贵者,行贿弄巧,施尽龌龊手段,只求举为孝郎廉,即使被人污了妻女,他亦视作平常,转而窃想:他淫我妻女,吾蛰伏不语,待我掌权执政,吾亦淫人妻女,不亦乐乎?此辈实乃猪狗不如。幸苍天有眼,善恶自有报应,后人当戒之。
此处所言却是另番跷蹊事,一心向建之顽儿,入他后娘,且不题,却淫人妻女,那被污人家老爷反与他孝廉郎做,真个是旷古绝今;不曾再有,遂辑之惯于世人,仅博一笑耳。
却说世宗嘉靖中叶,权臣严嵩把持朝政,士大大趋附若云。
王老绾时年五十有二,他自幼父母双亡,由小便在故里浙江省余桃帮工混饭吃,壮年投军,后人严府听差,现置守门官职。
俗话说,宰相门人七品官,此话确然,欲巴结严太师之流,必先舍银子与老绾,故他守门虽仅七年,竟累积五万多两白银,连他自家亦不敢信。
子夜,其妻刘氏久不能寐,唯恐贼子自天而降抢了财宝,故虽年仅四十有七,却已熬成花甲老妇矣,王老绾嫌她渐觉腻烦,窃思:早晚去了也顺眼。
其子王景,年方十岁,生得獐头鼠目。人严府私塾充严太师之孙陪读,四年拲o本百家姓,子曰诗云之类,他仅知「关关唯鸠,君子好逑」数句。
逾年,刘氏偶染风寒速亡,老绾草草埋了不提。家里银两愈神愈多,他心里活络:「想我辛苦大半辈子攒下财富,景地尚小,花消亦少,趁现时还能动,为甚不寻欢快话一场?」他原想揣上银子至勾栏觅个相好,临镜自照,只见自家老朽呆纳,似那枯枝犒木,谁个瞧得起?他只得冷了心肠,闷闷不乐。
无巧不成书,另一门官肖三近日酗酒而亡,其妻唤做余娘,三十有八,虽是半老徐娘,却风韵尚存,乌丝云鬓,梨花带雨,粉妆素衣,掩不住饱满胸怀,遮不住撩情身段。王老绾早先识得余娘,惊?不已,现见她形只影孤,姿态迷人,心里便有那层意思,他又想人家人才一表,绝计瞧他不上,唯有太息,却了慾念不题,偶尔路见,亦垂头疾闪。
再说余娘自夫亡过,日子愈来愈据节,缘何?只因肖三平生嗜赌,今日若挣得十两,明日定输他十二、三两,他夫妻一直入不敷出,甚是紧张,肖三在时,尚借得到几两银子过活,而今却不方便。余娘来嫁肖三前,本是勾栏妓女,她虽有重操旧业之意,无奈珠黄人老,没几成卖相,嗟叹之余,徒自忧伤,虽有花三柳四来缠,不过贪一晌之欢而已,她思忖曰:「此时倘若有个财主,就算他无能行房取乐,只要一日三餐无忧,我也愿从他。」
正是:王老绾蓄财欲求伴。
风流妇窘迫忧三餐。
一日,王景闲逛,适值余娘外出,王景横跨一步,拦住余娘,露淫邪相,说道:「我听得说,你原是陪人睡的,新近没了相公,权陪我睡一睡罢!」路人闻言窃喜,俱闪一旁,看余娘作何对待。
余娘又气又恼又觉好笑。气的是众人俱无劝阻之意,分明欲看他笑话;恼的是丈夫新亡,便有人当众调戏,俟后光景可想而知;好笑的是当众逞强的竟是一顽皮小儿。余娘见他一双贼眼锥子样盯着自家起伏坠闪的胸怀,便知这小儿不是善类,她恼怒骂道:「黄毛小子,闪过一旁!」
谁知王景却是个胆大的,敢情平时依仗豪权放肆惯了。只见他自怀中掏出两锭白晃晃银子,硬要塞给余娘,一面理直气壮地叫嚷:「我不会白睡你,依了我罢,依了我罢!」
某人识得他来处,遥指严府道:「别小觑了他,他家老子是太师守门官,银子总是不缺的,可怜役了内室,谁从了他,也是享福的。」
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且说余娘正欲发作,听了旁人一席话罢,心里惊乍:「该不是月老牵线罢!」她拿眼瞅王景一阵,沉脸说道:「小子,这银子八成是偷来的罢!」
王景顿时红了脖子,扯直嗓门喊道:「笑话!我家多的是,装了满满的几柜子。」
余娘呵呵冷笑,只是摇头,她心道:「总想办法入他家,才知真假。」遂撇下王景,迳直欲走,众人哄笑,将散。
王景见众人笑得暖昧,以为众人俱疑他偷人银子,只急得一蹦老高,恨恨骂余娘道:「卖肉的,挨千刀的,你才偷人银子哩!还偷人哩!」
余娘听他污言秽语,正中下怀,佯装怒极,返身,拎王景左耳,迳奔严府大门去,口中发狠道:「我找你家长评理去。」众人见事闹大,悄然四散。
话说王老绾侍立严府门坊,远远见一绝色妇人扯着自家小儿过来,他便知定是王景又惹了祸,乃挤笑颜遂迎上去,不待余娘开口,他先请罪道:「小娘子,犬子开罪与你,实乃为父之过,望释了他罢。」
余娘抬眼,见一萎缩老儿至诚鞠躬,心中惋惜:「我见他儿年小,还以为他正值虎狼之年,谁知却一老五,奴家命薄。」她强笑答道:「官人勿惊,实因汝儿欺人太甚,我方擒他来。」
王景却不服,争辩道:「父亲,她说我偷人银子,我才骂她偷人。」
「放肆!」王老绾斥喝,抬头一望,才知绝色妇人是余娘,他见她杏脸桃腮,体态丰腴,不禁旧念泛起:「今生若得她陪睡一遭,即便即刻死了,也是值得的。」欲心飞掠,急火攻心,霎那,老绾胯中软物凭空撑起,硬挺热烫,大异寻常,他怔怔道:「肖三乃吾同门,小娘子有甚难处,但说无妨。」
余娘本欲离开,听他言辞,便知老儿起了邪念,转而思忖:「他虽其貌不扬,穿戴倒也齐整,亦非没荡之辈,将计过活原是不赖,只是他的银子。」余娘拿捏不定,一时无语。
王老绾见她沉吟不语,秀眉壤春,别有风韵,不由呆了。他只觉腰中硬物挺翘,无法收拾。时值换班,另一守门官戏言:「汝去罢!余娘亦是单身,乾脆你俩凑一处罢。」
余娘佯怒,疾行,王老绾跌跌撞撞见追不舍,他深深一揖,说道:「小娘子若不嫌弃,请至寒舍小坐。」
余娘不言语,心里乱念迭起:「想肖三旧时,日进十多两银子,可惜全花了去,若存积些,妾身何至今日这般狼狈!挑个行货大的,你贪我爱,快活至极!
也罢,权去瞅瞅,适机试试老儿功夫,若还过得去,从了他也无妨!他已是半百老儿,待奴家施展夺命绝招,催他到了地府,银子便是我的!」
不说余娘心如蛇蜗,单说王景见妇人胸襟凸起,宛若一对玉碗倒扣,他壮胆把手去摸把握不住,又软又硬,美妙无比,王景大道有趣,他见余娘扬手将打,忽闪一旁,只是笑。
王老绾大窘,奔上前扇他两耳光,怒骂:「无耻之举,小娘子乃他姬化身,怎敢放肆!」王景啼哭道:「八成你看上他了,亦欲摸耍,见我抢先便扇我。」
「滚!」王老绾听被王景说破心事,不禁火冒三丈,猛的一推,王景跌坐在地,号哭不止,余娘懒得理会,埋首随王老绾而去。